关于电影好不好看,大家去电影院检验吧,今天想说一说《芳华》的编剧,也是当代女性文学作家中实力被严重低估的一位——严歌苓。

曾为文艺女兵的严歌苓,她说《芳华》是她最诚实的一本书,有很多对那个时代的自责和反思。
也许你没有读过她的小说,但你一定看过她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。陈冲导演的《天浴》,张艾嘉的《少女小渔》,张艺谋的《金陵十三钗》和《归来》,陈凯歌的《梅兰芳》,以及孙俪演的电视剧《小姨多鹤》,蒋雯丽主演的《幸福来敲门》,陈数主演的《铁梨花》,赵薇演的《一个女人的史诗》....每一部作品都打动过无数人。
《芳华》小说原名叫《你触摸了我》,同样出身部队文工团的冯小刚,在看过之后当即决定要把小说拍成电影,并改名为《芳华》。

严歌苓是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最多的作家。她的小说,都有强烈的故事性和画面感,以至于很多人看了都有这样的感觉:看严歌苓的书就像在脑海中放了一部电影。导演们喜欢拍她的作品也是因为:不需要怎么改原著就可以直接拿来当剧本了。
不仅如此,她还是中国极少数受过西方创意写作训练的作家,不仅能够双语写作,还是好莱坞专业编剧。

严歌苓本人,气质优雅从容
另外,大胆的创作题材、独特的女性视角也是严歌苓作品与众不同的特征。
在严歌苓的作品中,有讲述女同性恋故事的《白蛇》,有讲大陆移民生活的《少女小渔》和《扶桑》,有讲赌徒的《妈阁是座城》,有讲老师和学生不伦恋的《老师好美》,以及多部讲述文革时期、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,填补了文学创作上的空白。
另外,她的作品尤其偏爱刻画弱势女性,妓女、女同等这些充满戏剧冲突的形象。她与同时代女性作家亦舒、张小娴也完全不同:严歌苓从不洒鸡汤、不写狗血的爱情故事,她的作品里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,而是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苍凉,和不同时代下女性面临的困境。

《金陵十三钗》
《白蛇》——与李碧华的《青蛇》隐约的百合意味不同,《白蛇》讲述了女同间朦胧的恋爱关系。
文革期间,落魄的女舞蹈家“美女蛇”孙丽坤,每天面对着终日的看管和监禁,以及门外建筑工们的轻视和调戏,在无望的生活中渐渐放弃自己。终于,一个从小为女舞蹈家倾倒的小女生徐群珊,长大后扮成男性“徐群山”来看望孙丽坤,每天看她跳舞,两人很快陷入了炙烈的爱,孙丽坤也找回了风采奕奕的自己。但很快,她发现了徐群山的女性身份,一时得了抑郁症。在医院,她们以同性的身份正常交往,如同恋爱一般,但最后还是各自结了婚。
无论是孙丽坤还是徐群山,都跳不出时代带来的局限性。她们爱着对方,却对两人的相处感到“恶心”,女人和女人怎么可能“搞起来”呢?在书中,吃瓜群众本来对她们手牵手、眉目传情很是疑惑,但验明正身之后却失望的表示:
再往后大家对她们俩丧失了兴趣。再亲密、再钻小树林都没看头了。女人和女人有什么看头?
孙丽坤觉得,这种爱是需要“纠正”的,而徐群山则把一切的爱意归结于“我很小的时候特别迷你”。
珊珊在他身上可以收敛起她天性中所有的别出心裁。珊珊天性中对于美的深沉爱好和执着追求,天性中的钟情都可以被这样教科书一样正确的男人纠正。珊珊明白她自己有被矫正的致命需要。

电视剧《幸福来敲门》,根据《继母》改编
而《扶桑》,更是深刻的回答了一个问题:被骗到美国的“妓女”是怎样一种存在?
一百多年前的美国旧金山,第一代中国移民生活如蝼蚁。廉价的中国劳工、被拐卖来的妓女、流民、小偷、酒鬼挤满了肮脏的唐人区。妓女扶桑,被卖了之后,不哭不闹,吃的下,睡得着,有男人爬上她的床,她顺从,她迎合,然后把自己洗干净等待下一具肉体。
扶桑像任何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一样,受难,宽容,生长。和《天浴》里的文秀一样,她们是传统中国女性的代表——她们无声无息,但包容万物;她们身上,都有一种看不见的隐忍。

《天浴》
这种隐忍,像我们的母亲、像我们的民族,严歌苓把中国人的母性描写得细腻而深沉,朴素而温暖。
在《少女小渔》中,严歌苓刻画了一个移民到美国、为了绿卡,在男友安排下嫁给一个长自己几十岁、穷困潦倒的意大利老头的“佛系”少女小渔的故事。
虽然小渔只有十七岁,但她从骨子里就透着母性的光辉。因为善良,所以对男友顺从,对躺在病床上的人都心存怜悯。

电影《少女小渔》
在院子大门后面,他将她横着竖着地抱了一阵。问她:“你喜欢我这样吗?”她没声,身体被揉成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。第二个周末他与她上了床。忙过了,江伟打了个小盹,醒着他问:“你头回上床,是和谁?”
小渔慢慢说:“一个病人,快死的。他喜欢了我一年多。”
“他喜欢你你就让了?”江伟像从发梢一下紧到脚趾。小渔还从他眼里读到:你就那么欠男人?那么不值什么?她手带着心事去摩挲他一身运足力的青蛙肉,“他跟渴急了似的,样子真痛苦、真可怜。”她说。她拿眼讲剩下的半句话:你刚才不也是吗?像受毒刑;像我有饭却饿着你。
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,没有闲情逸趣的小资情调,也没有因为命运而感伤怀恨。严歌苓笔下的女性是来不及思考的,生存的危机紧紧地压迫着她们,时代毫不留情地拉扯着她们。她的笔触,冷静而孤独,冷酷而直观,但,却永远透露着一股“熬到头就有希望”的信念。

电影《少女小渔》
这样独特的视角,和严歌苓戏剧性的人生经历分不开,而严歌苓本人也像她笔下的女性,坚强而温暖。
生于 1958 年的严歌苓,有着并不温暖的童年。父亲是作家萧马,但在阶级斗争中被打为“右派”,后来父母离异,萧马与演员俞平结婚,小小的严歌苓有了继母。
12 岁,她被选入部队文工团学习舞蹈,一入部队就是 15 年。在文工团,她爱上了一位年长的男性却反被对方出卖,几乎使她身败名裂。在苦闷中的严歌苓开始了笔耕生涯,而这一写就停不下来了。
在出国之前,严歌苓已经很有名气,并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她到美国进修,对当时的写作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严歌苓回国后痛下决心,一定要去美国学习。于是,身为 50 后的她苦练英语,只用了一年的时间,托福就考到了 577 分。1989 年,严歌苓赴美留学,进入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就读,获写作硕士学位。

电视剧《一个女人的史诗》
对写作,她除了发自内心的热爱,还有中国当代作家、编剧身上普遍缺乏的最重要的东西——职业精神。
一个文学作品、剧作品要有时代穿透力,最基本的便是要真实。为了追求自己作品的真实,严歌苓会为了写作体验不同的人生。
严歌苓说自己经历过无数个人生——为了写《小姨多鹤》,她专门去日本住在长野一个村子,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;为写《妈阁是座城》,刻画赌徒的心理,她去澳门赌场赌钱;为写《陆犯焉识》,她又特地去青海劳改农场采访;为写《第九个寡妇》,到农村去种地,挖红薯;为写《上海舞男》,就去跳舞,体验为舞男争风吃醋的感觉...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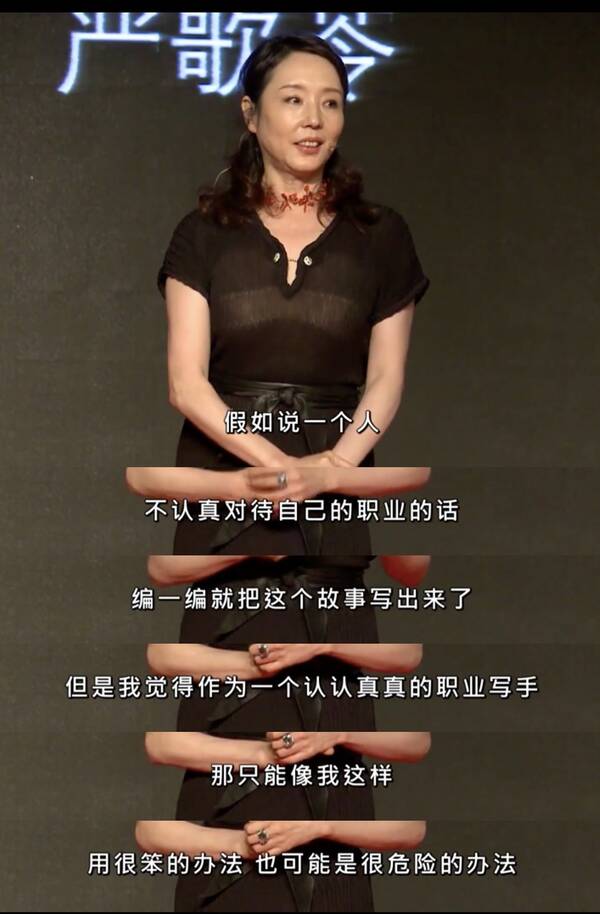
去体验别人的人生都是要花钱的,严歌苓说自己是攒钱够了才决心去的日本,而有些故事的挖掘很费时间和金钱,如果不被改编成电影,单靠发行小说根本“回不来本”。
还有一些故事,像《陆犯焉识》,严歌苓知道有可能出版不了,但她还是写了,因为“自己身上有一种使命感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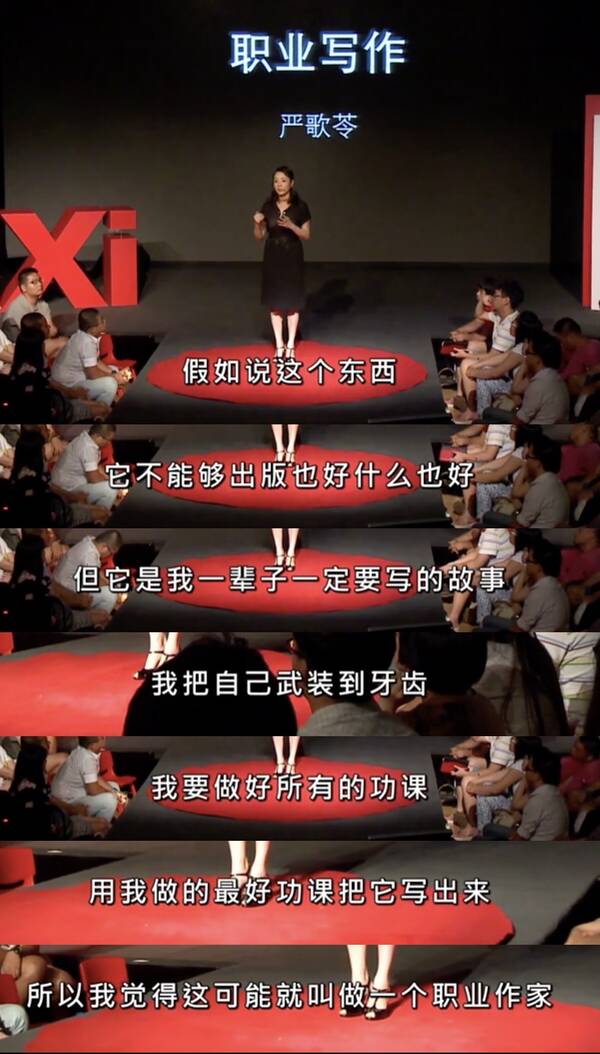
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严歌苓的作品总是被导演们青睐的原因,除了一段段人们不该忘却的历史,还有作家足够的热情和反思。
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剧作家,我就是一个小说家。我从不觉得自己改编的剧本有多好,小说的写作要比剧本的创作好出一大截。写小说就是把一个想法或一个故事,通过虚构来创作一个事件,赋予每一个人生命力,你是造物主,这是与编剧完全不同的,没有人会干涉我,我对自由是很看重的。
——《严歌苓:我经历过无数个人生》(凤凰网)

![]()